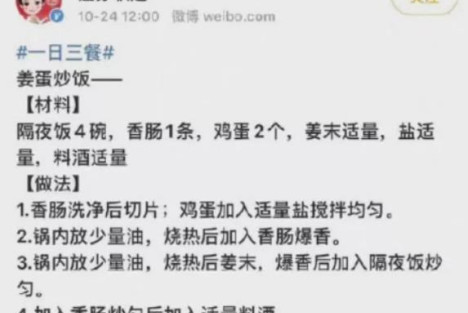为什么要建立新的中国法律与现实的研究——《过去和现在》序言
作者:黄宗智
中国传统法律在近百年中经历了三次极其沉重的打击。第一次是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在列强逼迫下,为了重建国家主权而大规模移植西方法律,几乎完全抛弃了传统法律。第二次则是在现代革命运动中,从解放区时期到毛泽东时代,既否定了国民党引进的法律,也再次完全否定了中国传统法律。前者被认作”资产阶级”法律;后者则被认定为“封建主义”法律。当时,旧传统的方方面面中唯一被肯定的是乡村习俗中的调解。第三次是改革时期,再次全盘引进西方法律,既抛弃了毛泽东时代的现代革命法律传统,也再一次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法律。“现代”被等同于西方;中国传统被等同于不能适应现代化和市场经济需要的“前现代”或非现代。
经历了这样沉重的打击之后,中国的法律传统等于是被完全从当前的现实隔离了开来。它可能带有历史价值和中华民族的智慧,但它不具有对现实生活的意义;它可能有助于理解历代王朝,但对今天的现代化和市场化日程、对国家新的立法、对人民的实际生活,被认定为几乎毫无意义。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只可能日益衰落。当今全国各大法学院的课程和研究都只可能以西方的现代法律为主。无论是法理领域还是各部门法领域,所用教材和所作研究都完全以欧美法为主。与蓬勃发展和日益扩张的新法学领域相比,中国法律史日益被边缘化、所起作用日趋式微、在各大法学院所占人员比例越来越小。在青年法学者的培养之中,可以说基本不起什么作用。事实是,中国法律史研究领域今天正处于一个极端的困境,甚或可以说是个绝境。
与现实隔离的法律史领域
经历了三次重击的中国法律史领域,幸存的基本只是完全脱离现实的纯学术研究,主要是思想史和制度史。但是,首先应该说明,在这两个领域的范围之内,不少学者作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对传统的法律思想家、论著、法典、制度设计等等都有相当严谨和细致的叙述和梳理,为进一步的研究积累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有的学者更突出一些重要的概念,比如强调礼仪、道德思想在中华法律系统中所占的地位,指出伦理在法律思想和制度中的重要性;有的强调中国法理中法律和情理的并用,区别于现代西方法律;有的说明了汉代以后中国法律传统在严厉的法家制度之中掺入了儒家仁政、和谐的理想,即所谓法家的儒家化;有的强调中国社会中的调解传统,强调其和谐理念的优越性,等等。当然,其中也有一定的民族感情性的表述,强调“伟大”的中华民族法律传统,体现了新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这里没有区别法学学科和历史学科中的法律史研究。两者虽然有一定差别,但在这里指出的一些基本性质上,大同小异。)
但是,总体来说,这样的研究都缺乏现实含义,不能够超越中国传统法律百年来被一再否定的历史背景。受到的打击是如此之沉重,即便是法律史专业的人员,许多也在有意无意中基本放弃了自己对当前现实和立法的发言权。即便是强调今天必须继承伟大的中国传统法律的研究,也多局限于一些宽泛的意见,没有针对现实或立法需要提出自己的具体的见解,也没有对当前的西方现代主义主流法学提出具体的质疑,结果等于是默认唯有西方法律方才适用于当前的中国。
这样,法学与法律史都长期处于一种非此即彼中西二元对立的认识框架之中,也等于是说,一个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全是全非框架之中。当然,来自毛泽东时代的高度意识形态化思维习惯肯定也是一个因素。无论如何,研究人员就连在研究过去的法律中,也常常很自然地放弃了自己的现实感。多年来的中国法律史研究多倾向于一种为思想而思想的研究,不多考虑到司法实践;或者是为制度而制度的研究,而且仅仅是设计意义上的制度,不是运作意义上的制度, 不多考虑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最终几乎等于是一种“博物馆”珍藏品似的研究,缺乏对实践的关心,以及对过去和现在的现实感。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学者甚至形成某种(或许可以称作)“珍藏品管理人员意识”,一方面坚持中华法律的伟大;另一方面,坚持中西法律非此即彼的完全对立,也就是说,传统法律与全盘西化的今天的立法现实完全无关。对于试图跳出这种二元对立框架的研究,以及把中国传统法律从博物馆搬移进入现实和现代社会的尝试,有时候难免会直觉地反对,甚或感到是对自己的珍藏品的一种威胁。
在我看来,如此的研究正反映了这个领域的特殊历史背景。说到底,这种学术领域的倾向乃是来自旧法律传统一再被国家领导者和立法者完全否定的结果。正因为中国现代的法律几乎完全是从西方引进的法律,新法律代表的是一种没有历史的虚无意识,而旧传统代表的则是一种没有现在、没有将来的历史。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方面。当然,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发出要振兴中国自己的法史研究和跳出这种绝境的呼声,甚至尝试了新的研究路径,但是,就法律史领域整体来说,仍然不可避免地被置于与现实隔离的基本状态之中。
法学今天在认识上和精神上的分裂状态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前的法学显示的是一种认识上和精神上双重意义的分裂状态。一是占据主流的所谓“现代”法学,把“现代”法律完全等同于西方法律;同时,研究法律历史的不关心或放弃对现代法律和对现实的发言权。正因为如此,两者基本互不对话,互不影响。在研究倾向上,两者同样倾向于偏重理论和制度,缺乏对实践和实际运作的关怀。我们如果以人来比喻社会,这等于是一个人完全拒绝把自己的现在和将来与自己的过去连接,把自己分割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这是第一层意义上的分裂。
另一层意义上的分裂,是感情与认识上的分裂。有的研究人员在感情上认同中国和中华民族,充满爱国精神以及对国家对人民的关怀;但是,在认识上,则完全认同于所谓“现代”法律和法学,认为(或起码不反对)西方现代的是唯一真正意义的法律。鉴于国家领导者和立法者百年以来的意见,大部分的研究人员也只可能属于这样的观点。这样,感情和认识对立,形成一种精神上的深层分裂。上面所说的坚持中国法律传统与西方法律的完全对立,以及卫护中国法律的特殊性和珍藏品性,便是这样的分裂状态的一种表现。两种倾向其实是同一“情结”的两个方面。
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只可能日趋式微。一方面,法学领域主流完全被源自西方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占据。另一方面,法史学界完全自我束缚于传统法律已经完全过时的基本信念,并因此也只可能在教学之中面对一代又一代越来越不关心中国传统法律的青年学生。
建立新的视野
首先,应该说,这是个完全可以理解的状况,是中国百年来在内忧外患压力之下所导致的状态;但是,同时也要说明,它是个违反我们基本的历史感的状态,是个不正常的状态。历史当然既有断裂也有延续,但是绝对不可能是完全断裂的。好比要了解一个人,绝对不能忽视他前面的大半生。再剧烈的革命,也不能完完全全地割掉过去;再戏剧性的变化,也不可能完全改变一个人——亦即所谓本性难移。
从历史实际的视野来看,中国今天的法律明显具有三大传统,即古代的、现代革命的和西方移植的三大传统。三者同样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实际存在的、不可分割的现实;三者一起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中形成一个有机体,缺一便不可理解中国的现实。但今天的法学界主流把“传统”仅等同于古代,并完全与现实隔离,又把毛泽东时代的法律传统既排除于“传统”之外又排除于现在之外。也就是说,完全拒绝三大传统之中的两者,要求全盘移植西方法律。
今天,我们不应该接受这样的状态,我们需要更清醒地认识,一个没有过去、没有历史的法律和社会是一个不实际、也不健康的法律和社会。过去的脱离实际的认识是被逼出来的;今天中国已经完全有条件走出这种认识上和精神上的困境,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包括古代和近、现代的历史,不仅是为了要更好地认识过去,也是为了要更好地认识现在和将来。
我们应该承认,上述的困境,部分来源是中国法律史领域的自我束缚所致。要建立真正的自我认识,一方面需要对当前整个法学领域中的西方现代主义进行深刻反思,另一方面需要对自己领域的研究倾向进行深刻反思。简单地否定自己的历史,对法律采取一种没有历史的虚无态度,乃是今天走到极端的现代主义的深层构成原因之一。同时,忽视过去的实践,虚构了一个没有活生生意义的法律史,怎能对极端的现代主义、全盘西化主义进行反思?从没有现实意义的基本前提出发的法律史研究,怎能构成中国自己在法律领域中的主体性?在这样的自我束缚之下,中国法律史研究怎可能不被完全边缘化?
超越本土东方主义
接受百年来对自己的历史的拒绝,便等于接受一种本土的东方主义,认为中国传统只是一个“他者”,只适合用来突出西方现代法律的普适性。在研究中如果只试图说明中国自成系统的法律思想和制度,只为过去而论过去,满足于简单的思想史和制度史,即便是充满民族感情的叙述,最终的现实意义只可能是作为西方现代法律的“他者”。
正因为如此,中国今天要走出这个困境,需要推翻现在的这个前提性信念,重新塑造我们对中国过去和现在的认识,建立中国法律史对理解过去和今天的现实的必要性。首先要跳出不顾实践和实际运作的研究架构。如果简单地仅仅着眼于理论,中国法律史在近百年中所经历的确实是一再的巨变和反复。从以德国为模范的晚清和中华民国历史开始,到毛泽东时代的反封建、反资产阶级法律,再到改革时期的再度全盘模仿西方的经历确实是一个巨变的、断裂的过程,其中古代法律确实似乎不具有任何意义或正当性,而革命的现代传统则在改革时期被置于与清代法律同样的地位。光从理论和法律条文来看,中国近百年的法律历史确实似乎是一个完全虚无性的变化,没有什么历史延续和积累可言,几乎可以比喻于一个性情非常浮躁、易变的青年,谈不上经验和积累,更谈不上历史和传统。
但是,我们如果从法律实践的视角来考虑,近百年的历史展示的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图像,其中当然有变迁,但是,也有延续和积累。也就是说,现实有它一定的历史,并且不可脱离历史来理解。实践之不同于理论,首先是因为它具有主体性,不允许简单的全盘移植,而要求在实践中,也在法理中,适应中国的实际,包括人民的意志。第二,实践要比理论宽容。它允许中西合并、相互拉锯、影响、协调、妥协。而法律理论则不然,它要求逻辑上自洽。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如果限于理论/思想研究,便只可能与西方法律相对立,非此即彼,绝无可能相互并存、相互作用。但今天中国的现实不允许这样简单的选择,既不可能复古,也不可能脱离中国历史而全盘西化。中国现实所需要的,正是共存和相互影响。第三,最最关键的是实践法律史的现实意义。脱离了实践,只论理论,便谈不上中西的取长补短,更无庸说建立可以在现代世界中适合中国实际的、独特的法律。
这里要倡导的是建立一种新型的、关心实践和运作,也就是说现实世界的中国法律史研究。理由首先是实践历史要比理论历史贴近历史实际,而正是面对历史实际,我们才有可能跳出百年来中国的自我否定和历史之与现实隔离。我深信,唯有如此,才可能脱离当前的法史研究绝境,才可能把中国法律史从博物馆中挪移出来,重建中国法律历史的现实意义,重建中国法律历史在全世界的法学和法律中所应有的地位。本书的主旨便是要阐释和证明这一点,并试图在中国法律的实践历史中探寻能够适应当前所需要的、融合中西的自主性和现代性。
同时,应该说明,我提倡的实践历史研究,乃是一种手段性,而不是终极性的建议。突出实践历史是矫枉过正的策略,是针对过去偏重理论、表达和制度,无顾实践和现实的手段。但这并不是说历史只是实践的历史,或者说唯有实践才是真实的。很明显,实践只是宽阔的历史和现实中的一个部分,它绝对不能脱离理论和表达。它本身既可能是合理的,但也很可能是不合理的。而且,它本身缺乏前瞻性的理想、理论性的洽合,以及精确、系统化的概念。很明显,实践是需要道德理念和理论的前瞻性的,不然,它只可能是回顾性和经验性的。这也是本书特地突出中国的“实用道德主义”思维方式的理由之一。作为具备极其长期的历史生命的传统,它有一定的优越性,是我们今天可以继承的一面。另外,我的研究一直强调清代法律的基本性质绝不简单在于它的表达,也不简单在于它的实践,而是在两者的矛盾结合,其中既有张力和冲突,也有妥协和协调。它才是中国法律传统的长期持续的真正秘诀。我真正要提倡的是在宽阔的历史观和现实感中,确认历史既包含物质层面、也有思想层面,既有社会经济结构也有能动,既有制度、也有过程,既有变迁、也有连续,既有大的历史趋势、也有偶然性和个人的抉择。我们需要的最终是从宽阔的历史视野和现实感来理解中国法律的过去和现在。
我们如果回到法学领域来说,过去的思想史和制度史研究乃是重要的资源。它需要的是实践和现实的层面,以补其不足,但这不是要抛弃过去的研究。最终,我们所要的是实践和思想的综合,也就是说新研究和旧研究的综合。这样,中国法律史研究才会在新时代具有真正的生命力。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