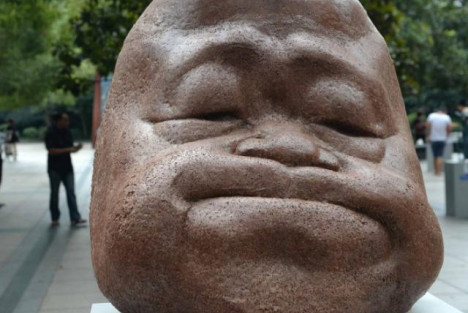哲学的两个思维方式和比较哲学的两种基本方法
哲学的两个思维方式和比较哲学的两种基本方法
—在人民大学国际中国哲学与比较哲学研究中心成立会议的发言
田辰山
2009年7月25日
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
现在比较哲学方法基本上有两个:一个是西方比较法,一个是参照中国角度的比较方法。比较哲学方法其实也是思维方式和做学问的方式方法,是这个意思上有两种比较哲学的基本方法。也即,中国和西方各自是两套思维方式、两个传统、两套方法论。这里需要指出,其实“方法论”一词说中国有什么方法论,也不合适。但是今天我们没有别的语言,还得用这个词说问题。但已经不是西方那个方法论—methodology,而只是说明中国有一条路,西方是一条路。中国是互系性方法的道路,西方是二元对立的方法。是这样两种基本比较哲学方法。
今天讨论比较哲学方法这个题目之所以很重要,其实也是把中国和西方这两套思维方式搞清楚。这在今天是非常重要的。今年五月《文史哲》杂志召开了一个会,请了十几个学者专门讨论现代中国学术界使用的话语问题。这表明,现在到了中国学术界对我们一百年来使用的话语加以认识的时候了。我是持这种观点的,即一百年的话语是有问题的,这个话语是从西方来的,这个问题是什么,现在需要对这个问题有意识了。
今天上午赵敦华老师讲了同源分流问题。讲人类开始都是从非洲来。讲的是考古和基因分析。如果说这个说法是成立的,你如何把考古、基因分析与思维方式、哲学、文化联系起来,其中的必然学理关系是什么,这是需要找出来的、说清楚的。
我想提及的是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的思维方式差异。我举一个很平常的例子。比如说进行刑侦破案的例子。通过破案做法联系到传统思维方法问题,引出中国是个“道”,西方是个“上帝”方法。它必然联系着比较哲学方法问题。我觉得是比较能够说明问题的。
如何是一个破案的方法问题呢?比如说现在出了个人命案,谁是凶手,什么线索都找不到。怎么办?中国的方法是既然如此,就将侦查暂时搁置、等待。等到什么时候出了新情况、有了新线索再重新追查。我们是非常实用地办事的。但是西方遇到这种没线索的情况怎么办?没有线索也不成,心理上不踏实,也得要想象出什么来。于是,谁是凶手的线索是可以假设的,假设是某某干的,之后根据假设是这个人干的,去推理原因,去监视,去调查,就有一大堆事情可做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哲学问题。从哲学角度,方法论的问题是同一个。刚才讲“同源”。其实“同源”的根本点是中国和西方大家都是人类。不能说一个是猴子,一个是人。都是人这点上毫无疑问是有共同之处的。这点比“同来自非洲”的说法要强有力得多。但是这否定不了人和人差别很大。不能用共同之处埋没了差别。用通变来说,没有差别就谈不到共同性,共同性就不存在意义。共同性是在差别相对之下产生意义的。买一斤黄豆,对一粒粒的黄豆的共同性的思考还有意义吗? 这时看到一粒粒黄豆之间有差别反而很有意思。
我认为的一个相同方法论的问题是,在原始人类阶段,远古时候,中西方可能都碰到同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这个世界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读中国古代典籍,读西方古代思想家,都可以找到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方法上的不同。这也可以说是今天这个比较哲学方法最开始的一个差别问题。西方的问题恰恰是一个假设性思维方式演变而成的方法。因为没有人搞得清楚这个世界是从哪里来的。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无法得出定论。所以对这个问题,中国人的态度是放在一边,不再去毫无根据地苦思冥想。我们关心的、演变为思想方法的是要看现在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行的,宇宙、自然是怎么运行的,人是怎么生活的,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办,就是通过观察总结出一些观念。这个观念什么语言还都不能说清楚。所以《道德经》就有了“道可道非常道”。也就是说,知道有这样一种东西,但是这个东西远非我们言语所能表达。也可以说,你用任何语言来说它,就要出问题。老子说“道”这个字本身也是有问题的,也是强说的一个字。
中国人思维方式是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借助英文词汇说明一下。英文有个“what”(什么),还有个“how”(如何)。中国人不追求“什么”,不追求是谁、是什么创造了世界,因为是无头案,琢磨它是无用之功,而只是看这个世界是“如何”的。中国人是通过观察和思考的方法,看出道道来,总结出一套道理来。这就是成中英老师讲的观和感。西方人恰恰是一个假设的方法。上帝是假设出来的。世界是从哪里来的无从知道,需要假设一个实实在在有那么一个实体。假设之后在假设的前提之下进行论述、推理等等。所以西方思想传统和学术就是假设,时间都花在围绕类似上帝这样一种假设实体的概念。上帝存在不存在,它怎么开始制造世界的,定了什么法则,世界、历史怎么开始,人是什么等等,有了一整套围绕上帝的说法。神学除外,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科学都是用上帝连在一起走的一条路。福山提人类历史终结,亨廷顿说还没终结,还有文明冲突。所以一切学问难是围绕着这么一个东西在转。
也就是说,西方学术实际整个是一套形而上学的方法。不过,这个形而上学的方法不是《易经》所说的形而上。我们用“形而上”作了西方“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一个翻译。但是中国《易经>》的“形而上”不是西方的“形而上学”。西方的形而上学就是因为凭假设说话,先有一个前提假设,在它下面进行推理、找逻辑、论证,是这样一套方法构成的理论体系。这是非常抽象的工作过程,所以西方叫形而上学。这套形而上学,理论本身也好、方法也好,脱离不开一个上帝,整个的问题提出是上帝且围绕它展开。因此也就离不开思维方式上的二元对立。
中国采取的是回答问题的“how”,是揭示这个世界现在“是怎么样”的、“如何”的。根据当下这个正在运行的“how”的方式方法得出了是一种道的方式,或是阴和阳方式,或是五行的方式,我们有很多说法。正因为现在看到是这些种东西或者方式,宇宙、自然、人是什么及其它们什么关系,无非是一种延续和变化,也即“通变”。原始的东西是什么样和什么关系,也无非如此。所以,在中国这里,没有开始,没有结尾;开始也是结尾,结尾也是开始。而西方有一个确定的历史的开始和历史的结尾,人类有上帝安排好的末日来临那天。中西方就思维方式来说,是这样两个。
是这样两个思维方式说明中国思想传统和西方思想传统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上,采取了两个不同的路径,也即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方法;一个是回答“how”,一个是回答“what”。一个是回答“怎么样”,世界是怎样动作的,怎样运行的。中国的是什么方法论,还真的是不能够用西方的话语结构来判断。你如果用西方的话语结构判断,来做学问,你首先需要意识到,用的西方话语结构已经不是西方语言本来的词汇和概念和原有的意义。比如说本体论,成老师用了很多很多次这个概念。此外,一百多年来很多很多中国有名的学问大家用本体论这个概念。我觉得这种用法本身没有问题,它已经变成中国词汇了。成老师用它的时候,刻意要讲清楚什么是本,什么是体。但是现在变得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不少中国人讲的本体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但是原来的“ontology”,翻译成中文,来到中国学者头脑当中的这个“本体”概念,已经不是西方原来“ontology”的意思了。因为西方本体所指的就是类似上帝的东西,就是在把它作为前提假设思维之下的二元对立一套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逻辑。如果忘记了或搞不清楚这个情况,中国人讲的本体就跟西方的“ontology”混在一起了。西方人看到中国人用的本体,以为在中国可以用,是类似的一个东西。就把西方的“ontology”不自觉地、无意识地硬是强加在中国传统上了。也就是说,中国传统也是一套讲类似上帝的东西。所以,我们要讲中国思维方式,中国方法论是什么,西方的方法论是什么,是不能用西方的词汇和概念来回来去说的。这就是用西方话语讲中国事情出问题的地方。我还是同意安乐哲老师的观点,也是今天中国学界的一个说法,“西话汉说”是有问题的,“汉话汉说”是势在必行的。也即,中国是什么思维方式,什么方法论?是道的方法论,是易的方法论,是通变方法,即是中国思维也是中国方法论。。
谈比较哲学方法,可以说中西哲学过去一百多年来采用的比较方法,基本上是西方思维方式的方法。一百多年学术出的问题归于一点,是采用了西方的话语结构而对它导致的问题不自觉、无意识。现在是要使用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比较方法论。这是什么方法论呢?就是要有东西方比较角度,用东西比较话语来说中国的事情,说西方的事情。涉及一个西方概念,首先要在它所在的传统环境中去找到它本身原来的意思。中国的概念,要在中国传统环境中找到原来的意思。都找到了原来意思之后,再把它们拿来比较,而不是不问其两个思想传统本身的整个背景环境,只是拿一个西方概念作样品到中国来对号入座。可以说,现代以来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比较大抵是这样的比较方法,所以说,这样的比较方法存在很大的问题。
可以说,西方的思维方式,西方的方法就是神的方法,就是西方特有的形而上学方法,二元对立方法。中国的就是一种互系性的方法,看事物延续性的方法,看整体性的方法,整体观点是中国人的说法,也即互系性思维方法。比较哲学现在要着眼于这种方法,要创出一种东西方比较哲学的新模式。用比较通俗的语言表达,就是一个辩证的方法和一个形而上学的方法。按照郝大维、安乐哲的说法就是第一问题思维和第二问题思维方法。这个辩证法不是我们以往简单认为的,是西方传入的。这个辩证法跟西方的辩证法还不是一个概念。这个辩证法在中国人的嘴里和头脑里实际是《易经》、阴阳、互系的思维方式。辩证法在现代中国所用语言之中,只是出了同样问题的一个词汇而已。它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但已不是原来的含义。西方“dialectic”的意思恰恰是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这个问题必得要说清楚,要对它有意识。今天上午赵老师讲到什么东西都拿来比,说比较哲学很不成熟。但是我觉得如果更到位地说,所有这些比较方法都是属于形而上学、二元对立比较方法,都不是一种互系、通变式的;都是不问两个传统背景环境,只提出某单个概念,或者什么东西,到对方传统背景中去与雷同对象对号入座。比如孔子的历史朝代是一个动乱的朝代,柏拉图的时代也是一个混乱的时代,这就样将两人比较起来。而不是考虑到西方在哪个时期出现的柏拉图,西方那个时期的大背景是什么,与柏拉图构成着一种什么关系。柏拉图对后来基督教又起到什么作用,不是在整个域境背景之中找到柏拉图的思想,然后与孔子思想进行比较。如果一经这样顾及背景的比较,就会发现曾认为相似的地方,其实很大程度上不能比较,可比性很差,差别甚至大于相似。
认识差别是很重要的,不认识差别,你就不知道怎么和谐。你愿意和谐,你希望和谐,那都是属于人的态度,而态度不是问题本身,不是哲学问题。我们是讲哲学。我们心里状态尽管希望这样,但两个传统之间的差别是在那里存在的。是天天遇到的。讲同源,两个兄弟是不是同源?我跟我的儿子是不是同源?我儿子到了西方,几岁去的,长到二十八、九岁,文化上可说完全是西方人。我在中国生活那么多年,又在西方生活近二十年,我现在还是个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你说这是同源,这个差别是相当大的。我们俩话语很不一样,思维方式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你说今天谈中西方比较是谈差异重要,还是谈和重要?这得看目的是什么?不是对差别有独钟。我们谈差别的目的是为了理解,为了和。知道差别之后才会有智慧、才能将差别放在心上,然后去找到如何求得和谐的道路,去寻找一条道路、一个互相可沟通的方式方法。
西方离不开形而上学,离不开二元结构,离不开超越,离不开上帝,是离不开假设的。刚才讲同源分流,西方有人认为人类是从非洲来的,说实在的这还只是一个假设。尽管有基因上的证明似乎是,尽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说明,但还仍然不是定论。这就跟霍金的新理论一样,大爆炸理论也好,上帝创造世界也好,都不是定论,而是假设。爱因斯坦相对论当时认为是定论,迄今为止没有那么宏大的理论定论,以后总会有新的理论把它推翻。所以说在不是定论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把没有定论的东西看作假设。理论错误常常在假设阶段就是错的。
所以讲方法论,比较哲学方法论也是哲学的方法论,方法论是跟人的思维方式,人的世界观、人的价值观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是一回事情。只是你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东西,这就是一个方法。但是方法论也是世界观,也是思维方式,这是分不开的,也是语言问题,也是价值体系问题。从根本情况来讲,西方那套东西离不开假设,而中国不是靠假设来说明问题的。这是一个很关键、很根本的哲学方法和比较哲学方法的问题。
我认为可以用比较简单明了的话表明这一根本的方法问题。即一个是一多不分,另一个是一多二元。西方是一多二元方法论;中国是一分不多的方法论。西方的“一”跟中国的“一”不是相同的“一”。中国的是浑然而一的“一”,西方的是超绝的“一”,是外在的“一”,是由它开始单线的二元对立的关系。最原始的开始是“一”,它被假设为一个实体。我们从根本上要认识到这个情况。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现在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中国学界要开始探讨东西方两个思想体系根本差别在哪里。现在是用中国人思维方式来搞比较哲学的时候了。这是我的一个观点,谢谢大家。
为什么要指出中国百年来学术话语结构出的问题
—回应发言
刚才王老师讲的话基本上针对我的提法。因为中国近百年来使用的话语,我的观点是出问题了,很多学者认为出问题了。问题在那里?我认为分歧不在于是否承认语言变化的事实,不在于是否对语言变化采取接受态度;而是在于语言变化中的变化是什么,我们这套语言在今天出的是什么问题和为什么出问题。为什么要指出这个问题?
因为话语出的问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个表现就是全球化的形势,有了互联网和各种快捷传播和运输手段,我们跟西方前所未有地接近,频繁地接触和交流。但是互相的理解程度不能适应这种形势。比如,现在有大量召开的国际会议。但可以说很多人文社科国际会议都几乎形不成中西方学者真正的对话,都是西方学者讲西方问题,中国学者讲中国问题,各说各话,构不成直接对话。为什么构不成直接的真正对话呢?就是语言出了问题。我们现在用的是西方翻译成中文的这套语言,用来说自己的哲学问题,似乎对我们自己来讲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认为它可以表达中国思想,并无障碍感觉。但问题出在一旦返回去。这套语言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如果把讲中国哲学这套语言,用在跟西方人沟通上,这套语言再翻译回西方语言去,西方人是听不懂、丈二和尚的。是这个原因,要提出话语上出的问题。
还有的问题是政治上、外交上发生的。很简单的语言都与西方沟不通。我们以为“对不起”就是“SORRY”,认为“SORRY”跟“对不起”一样,是表达道歉的意思。但是美国人明明说了“Sorry”,但是却声明没有在说“对不起”,并不是道歉。全球经济在搞一体化,全球在搞单一化,但明显的现象是,由于距离近了,矛盾和误解的产生反而越来越多。是在这个意义上,需要提出话语出的问题。比如“人权”问题。这个概念在西方语言中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叫做“rights”?这与西方传统是直接相关的。文艺复兴以前上帝不允许人做的事情,人如果做了,都是“wrongs”,被教会判定是错的。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教会判定人不可仪做的错事,变得“OK”了。不仅可以做,而且还是上帝保护着做,判定为“rights”,是“做得对”的。这个“rights”(“做得对”)来到汉语当中,变成了“人权”概念。“rights”其实与“人权”风马牛不相及。因为中国人理解“权”或“权利”跟“rights”(做得对)根本不靠谱。中国人认为自己可为可不为,做得对,做的错,与权不权构不成一件事;一个是说东,一个在说西。再者,中国人讲做得对,做得错,不是由什么上帝(或普世标准)来评判和获准的。而是由人们考虑到社会各种关系之间的适当程度,不适当的我们认为是不对的,促成适当关系的则是对的。这个对和错完全是由我们自己来根据很具体的人事关系所进行判断的。
中国和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牛顶得很厉害。如果把这两套语言、她们所承载的思维方式、所表达的真正意思解释到桌面上来。误解能够解不开吗?如果还解不开,剩下的就不是人权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人权问题如果不是出于政治原因,是很可以轻松解决的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连语言的误解原因还没有搞清。所以在人权问题上首先话语结构是个大问题。
至于语言的变化,我对它没有什么质疑。我并非是在语言变化上表达自己的什么情感或价值取向的东西。我关注的是话语结构出的问题,是语言变化发生在什么层次上。你小孩说“哇塞!”——什么意思呢?当然在表达一种高兴,一种兴奋。这是在中国人所理解的层面上的意思。但是哇塞在其西方深层、语言背后的文化毕竟还是不一样的。还比如“再见”,我们讲“再见”丝毫不带有西方的宇宙结构,思维的结构。但是西方的“拜拜”(bye)是跟上帝相联系的。
说我们话语出了问题,我也不是主张语言不可以用。在中国环境当中,这套话语已经具备了中国意识,并非需要完全抛弃不用。但重要的问题是要懂得这套话语背后中西文化的差别。只有知道这种差别才能够更有效的使用语言,与西方交流的时候才能够把西方传统考虑进去,才能在交流语言上合理使用变化或把握。这时,你的语言才有可能让西方人听懂。在哲学、社会科学乃至文学艺术层面上的话语结构差别,是具有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的潜在风险的。在日常生活表面层次的中西方话语虽然也充满着结构性差异,但谬误性有更多实用和纠正机会,可沟通性还是强的。在这里说的是哲学,话语结构出了问题是需要严肃对待的,因为这是学术的本质要求。要考虑哲学结构上的差别,要明白这种差别,没有这种敏感你做什么学术?这绝对不是夸大,不是对它独钟,更不是什么喜好中西之间的争论,这种理解是扭曲了。对这个问题的意识程度不一样,有的人看的到,有的人看不到,有的人认为是严重问题,有的人认为小题大做,也是很正常的现象。正像瞎子摸象的故事,有人意识到的是腿,有人意识到的是尾巴。积极的态度是看到了部分,还想看到全身。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

|
|
|
|
|
|
|
|